金岳霖:我是個“哲學動物”
2013-01-28 15:56:29 作者:陽化杰 來源: 瀏覽次數:0
——《金岳霖回憶錄》讀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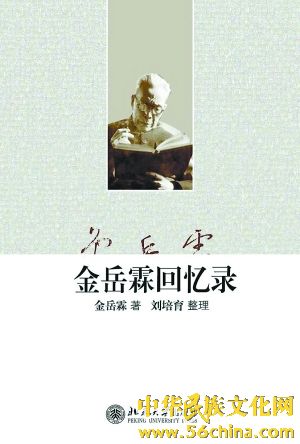
《金岳霖回憶錄》,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
金岳霖是一位大學問家,他在哲學、邏輯學等領域里都有很大的貢獻。我1964年考取他的邏輯專業研究生。雖然我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處,但我不一定能把握準他的治學思想。我“生不逢時”,投奔到金先生的門下時趕上了“四清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,10多年都是在政治運動和動亂中度過的。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學者,一般人對他都有一種敬畏的心理,因此同他深談的機會也不太多。我主要根據讀他的書,特別是在整理他的回憶錄時的一些感悟,談談他是怎么和哲學結緣的。
金先生16歲考取北京清華學堂,19歲以官費留學美國。開始學商科,因為“引不起興趣”,不久就改學政治學了。他認為,商業學與政治學相比,前者只是“雕蟲小技”,而后者才是直接關乎國家前途、命運的“萬人敵”的學問。他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都是寫的政治學。后來,金先生徹底放棄政治學而專心從事哲學研究,與他對政治學認識的改變有密切關系。通過研究政治學,觀察美歐以及中國社會的政治,他認為政治學“無科學可言”,政治領域里充滿了“玩政治”的行為,他對政治有了一種“厭惡感”。他在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中明確地說:“近年來對于政治——不僅是中國的政治,無論哪國的政治——極覺灰心,而對于哲學,頗有興趣。”(《金岳霖文集》第1卷,第210頁)
金先生對哲學的興趣達到怎樣一種程度呢?用他的話說:“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,我自己也是一個。”
金先生的兩部重要的哲學著作《論道》和《知識論》都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完成的。當年,金先生隨清華的師生從北京到長沙,再從長沙到昆明。金先生的《知識論》從昆明寫到四川李莊,又從李莊寫到昆明,一部六七十萬字的書稿終于完成。據金先生晚年回憶,那時候在昆明常有日帝飛機來轟炸,一次空襲警報又響了,他只好帶著稿子跑到北邊山上,他就坐在稿子上。那一次轟炸的時間長,解除警報時,天也快黑了,他站起來就走,稿子就丟到山上了。等他想起來趕緊跑回去找,已經不見了。一部花了幾年心血寫出來的稿子,一下子就沒了,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但是他沒有猶豫,“只好再寫”。一部六七十萬字的書稿是誰也沒有辦法記住的,所謂“再寫”只能是從頭到尾寫新的。金先生又花了幾年的功夫,終于在1948年12月寫成了。這部關于知識論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。金先生在《作者的話》中說,“《知識論》是我花精力最多、時間最長的一本書,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,我非常非常之高興”。金先生重寫《知識論》也成為學術界的一段佳話。
金先生研究哲學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邏輯分析方法。現在有必要談談金先生和邏輯的關系,以及他對邏輯研究的一些看法。
1980年,有一天我去看望金先生,問他是怎么樣搞起邏輯來的。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:1924年的某一天,他、張奚若和一位美國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散步,遇見一些人不知為了什么事情爭得很兇。他們三個人駐足傾聽,不自覺地也加入到辯論之中,張奚若和美國姑娘竟然各支持論辯的一方。辯論中有邏輯問題,可是他們當時卻不知邏輯是什么,于是便對邏輯發生了興趣。金先生晚年的回憶錄中也說到這件事,不過比較簡略,具體細節也略有不同。細思之,金先生對邏輯學發生興趣,并非那么偶然,那么簡單。在此之前,他讀羅素的書已接觸到邏輯。他欣賞分析哲學,必然欣賞分析哲學所使用的邏輯工具。說得再遠一些,金先生早在中學時代就有很強的邏輯意識,也可以說是邏輯天賦,他曾從民間諺語“金錢如糞土,朋友值千金”中推出“朋友如糞土”來;他也指出過《世說新語》中孔融對陳韙的反駁是不合邏輯的。這些都為金先生后來搞邏輯埋下了伏筆。金先生1925年底從歐洲回國,正趕上在清華教邏輯的趙元任先生調到中央研究院工作,于是金先生在1926年應聘到清華講邏輯。金先生搞邏輯不算是純偶然,卻是“無師自通”自學成才的。1931年他到哈佛大學進修,跟謝非教授系統地學邏輯。他告訴謝非教授:“我教過邏輯,可是我沒有學過。”結果引起謝老先生大笑了好一陣子。
上個世紀二十年代,現代邏輯還是一門很新的學問,國內懂的人很少。當時金先生接觸到現代邏輯的新成果,并且在自己的著作《邏輯》中同現代邏輯著名學者進行了對話。他后來對現代邏輯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金先生研究現代邏輯的主要目的,是要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哲學,構建一個完備的哲學體系。他認為,“邏輯就是哲學的本質”,搞哲學的人不能沒有好的邏輯素養。當時,邏輯課是清華哲學系的必修課,也是主課。
(劉培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。《金岳霖回憶錄》,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)
上一篇: 馬未都:"瓷之色"中見歷史
下一篇: 劉香成:填補民族記憶的空白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