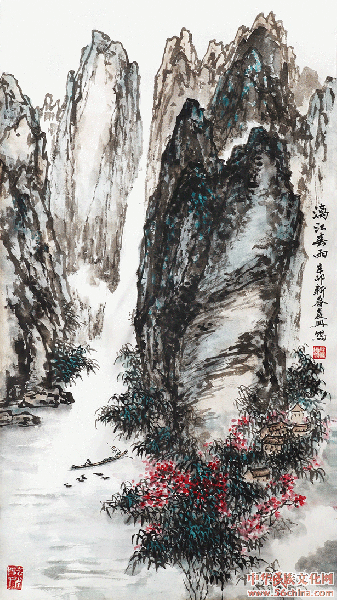馬治權書法欣賞
2013-03-04 22:55:34 作者:陽化杰 來源: 瀏覽次數:0
馬治權書法欣賞

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,書法熱的大潮席卷神州影響寰宇以來,在海內外我接觸過、教授過許多書法青年。馬治權就是其中一個。幾十年來,我親眼看到:他虔誠認真地沉下去,從祖國書法傳統(tǒng)的一點一滴學起,既研究書藝,又研究書理,更“書外求書”,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(yǎng),默默地筆耕不輟,步子走得是那樣穩(wěn)健,那樣堅實,那樣有力,以令人嘆服的修養(yǎng)、才華、氣質、藝術成就走在了中國書壇的前列。
很多年前,在陜西省機關職工書法展覽上,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字。像當時許多青年朋友的字一樣,有膽略有朝氣,潑辣大膽,令人感奮,雖不成熟,但幸好沒有染上追趕時髦的風習。他當時在省政協(xié)做文秘工作,還寫過幾篇引人注目的深沉而有銳氣的文章。后來,他改做編輯工作,廣泛地接觸了文化藝術界的朋友,這時他更感興趣的還是對書法藝術的追求。也就在這時,我和他的接觸就比較多了,他每隔一月半月總要拿字來讓我評價。我是目睹他一步步走出來的,他是屬于對中華民族書法文化的發(fā)展有使命感,對書法傳統(tǒng)執(zhí)著追尋,努力尋找書法中自我的青年人。
他自賦詩說:“炎黃文化五千年,博大精深氣為先。書道藝術其中嬌,獨具法則顯淵源。雖無眾色堪比畫,卻可與畫相理連,雖無聲音悅人耳,卻可妙過絲竹喧……”對中國書法傳統(tǒng)熾熱的愛使這位陜北漢子如癡如醉。幾十年來他每日堅持在工余早晚臨池學書達四五個小時。一本帖他臨過百遍仍不釋手。上大學逢假期,為了靜靜地專心習字,他一個人挾著一大堆紙,幾本字帖幾冊書論,躲到老家陜北的土窯洞里去練字、讀書。熱愛書法的青年中,像這樣投入的人實在是不多。
在楷書中,他扎扎實實寫過魏碑。《張玄墓志》、《張猛龍碑》、《鄭文公碑》他都下過很大的工夫。從用筆、筆勢、結字、字勢一遍遍分析,一通通臨摹,逐筆、逐字琢磨習寫,以至于可以通篇背臨。他還認認真真寫過顏真卿的《勤禮碑》、《東方畫贊碑》等帖。對顏真卿的筆法,他掌握得十分穩(wěn)健、準確,對顏的雄豪之氣,他也有比較透徹的了解,他更崇敬顏真卿的忠直剛烈。在沉入傳統(tǒng)之后,他不滿足于對古人的機械模擬,他在尋找自己的楷書面目。他苦苦地探索,企圖將顏書、柳書、魏碑楷書的優(yōu)點以自己的審美觀綜合取舍。他不斷地試寫,不斷地從技巧入手尋找新的書法面目與新的書法境界。在無數次的失敗之后,不協(xié)調的筆法逐漸統(tǒng)一了,不謹嚴的結字逐漸謹嚴凝重了,具有自己面目的字終于嶄露眉目了。我珍視他的每一點成就,為他的創(chuàng)新感到高興。楷書創(chuàng)新,多年來人們視為畏途,甚至有人以為今人再寫也超不過王羲之、顏真卿、柳公權、歐陽詢等古代大家。我對此論頗有異議,我覺得古人有古人的高峰,但絕不是今人不可逾越的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領風騷數百年。”今人只要決心大、方法對、意識明確,一定能超越古人,創(chuàng)造今天的輝煌。
在行書研究上,他在臨寫王羲之、顏真卿諸帖之后,特別喜歡何子貞筆法多變筆勢活潑的作品,對何子貞的《西園雅集圖序》等作品更是愛不釋手。由于他有了比較扎實的楷書基礎,更有明確的求新意識與途徑,所以寫起行書進步也比較快。在楷書和行書過關后,馬治權又開始浸淫隸書。他的隸書取法高古,下筆不俗。其中尤以《好大王》見長。《好大王》于清光緒初年出土今吉林省集安市。由于出土晚,清以前書家未能見到,所以馬治權的隸書很快就有了自己的面目。他將《好大王》的遒古樸茂和早年臨寫顏真卿的沉著雄厚結合在一起,形成了于渾穆中有一點簡散、于勁健中又流露著幾分婀娜的隸書,看他的隸書,讓人心生喜愛又多有肅然。
1994年上海《書法》雜志發(fā)表了他的既有“二王”筆法結體,又有顏、何某些筆法特點的行書對聯(lián);1995年《書法》和《中國書法》又對他分別作了專題介紹;2009年《書法》雜志又為他開了一年的專欄。《書法》雜志在國內書法界有較高的權威性和較大的影響,發(fā)表作品一向嚴格,在數年內連續(xù)對馬治權的作品和他本人予以介紹,這不能不讓人對他多年來苦學善悟的書道成就側目,也為他的刻苦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感動。
(鐘明善 著名書法家,中國書協(xié)副主席)
已有0條評論
查看全部評論>>